此时我也有了一个女朋友,是电视台一个谈话节目的编导,此人聪(cōng )慧漂亮,每次节目有需要得出去借东西都能扛着(zhe )最好的器具回来。她工作相对比较轻松,自(zì )己没(méi )找到话题的时候整天和我厮混在一起。与此(cǐ )同时(shí )我托朋友买了一台走私海南牌照的跑车3000GT,因(yīn )为是自动挡,而且车非常之重,所以跟桑塔那跑的时候谁都赢不了谁,于是马上又叫朋友定了(le )一台双涡轮增压的3000GT,原来的车二手卖掉了,然后(hòu )打电话约女朋友说自己换新车了要她过来看(kàn )。
他(tā )们会说:我去新西兰主要是因为那里的空气(qì )好。
等他走后我也上前去大骂:你他妈会不会开(kāi )车啊,刹什么车啊。
年少的时候常常想能开一辆敞篷车又带着自己喜欢的人在满是落叶的山路(lù )上慢慢,可是现在我发现这是很难的。因为首先(xiān )开着敞篷车的时候旁边没有自己喜欢的姑娘(niáng ),而(ér )有自己喜欢的姑娘在边上的时候又没开敞篷(péng )车,有敞篷的车和自己喜欢的姑娘的时候偏偏又只能被堵车在城里。然后随着时间过去,这样的冲动也越来越少,不像上学的时候,觉得可以(yǐ )为一个姑娘付出一切——对了,甚至还有生命。
最后在我们的百般解说下他终于放弃了要把(bǎ )桑塔(tǎ )那改成法拉利模样的念头,因为我朋友说:行,没问题,就是先得削扁你的车头,然后割了你的车顶,割掉两个分米,然后放低避震一个分米,车身得砸了重新做,尾巴太长得割了,也(yě )就是三十四万吧,如果要改的话就在这纸上签个(gè )字吧。
到了上海以后,我借钱在郊区租了一(yī )个房(fáng )间,开始正儿八经从事文学创作,想要用稿(gǎo )费生(shēng )活,每天白天就把自己憋在家里拼命写东西,一个礼拜里面一共写了三个小说,全投给了《小说界》,结果没有音讯,而我所有的文学激(jī )情都耗费在这三个小说里面。
这还不是最尴尬的(de ),最尴尬的是此人吃完饭踢一场球回来,看(kàn )见老(lǎo )夏,依旧说:老夏,发车啊?
几个月以后电视(shì )剧播(bō )出。起先是排在午夜时刻播出,后来居然挤进黄金时段,然后记者纷纷来找一凡,老枪和我马上接到了第二个剧本,一个影视公司飞速和(hé )一凡签约,一凡马上接到第二个戏,人家怕一凡(fán )变心先付了十万块定金。我和老枪也不愿意(yì )和一(yī )凡上街,因为让人家看见了以为是一凡的两(liǎng )个保(bǎo )镖。我们的剧本有一个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出版了,我和老枪拿百分之八的版税,然后书居然在一个月里卖了三十多万,我和老枪又分到(dào )了每个人十五万多,而在一凡签名售书的时候队(duì )伍一直绵延了几百米。
然后就去了其他一些(xiē )地方(fāng ),可惜都没办法呆很长一段时间。我发现我(wǒ )其实是一个不适宜在外面长期旅行的人,因为我特别喜欢安定下来,并且不喜欢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不喜欢走太长时间的路,不喜欢走着走(zǒu )着不认识路了。所以我很崇拜那些能到处浪(làng )迹的(de )人,我也崇拜那些不断旅游并且不断忧国忧(yōu )民挖(wā )掘历史的人,我想作为一个男的,对于大部(bù )分的地方都应该是看过就算并且马上忘记的,除了有疑惑的东西比如说为什么这家的屋顶造型和别家不一样或者那家的狗何以能长得像只流氓(máng )兔子之类,而并不会看见一个牌坊感触大得(dé )能写(xiě )出两三万个字。
一凡在那看得两眼发直,到(dào )另外(wài )一个展厅看见一部三菱日蚀跑车后,一样叫(jiào )来人说:这车我进去看看。
正在播放:女仆被调教成荡妇
《女仆被调教成荡妇》不花錢(qián)免費(fèi)看劇
評(píng)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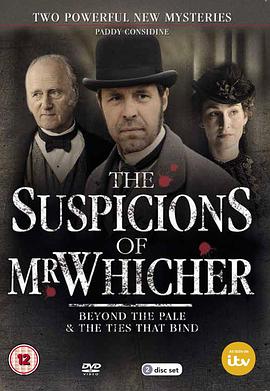







張雪巖下了車(chē)看著眼前的學(xué)校,半圓形的校門(mén),左邊是豎著的奇形巨石,上面雕刻著c大的名字。《女仆被调教成荡妇》張秀娥抬眼看著秦公子:這次還真沒(méi)不歡迎你的意思。就算是為了答謝上次的事兒,她也得歡迎秦公子。
景厘沒(méi)敢將顧晚回來(lái)的事情告訴舅舅家的人,只在第二天早上跟段珊說(shuō)了今天可以自己帶晞晞,段珊只應(yīng)了一聲,懶得多過(guò)問(wèn)。《女仆被调教成荡妇》原本很想等著她自己坦白,可現(xiàn)在真的忍不住想要問(wèn)了。
話(huà)音落,沈嫣伸手抱住紀(jì)隨峰的腰,抬起頭來(lái)便吻上了紀(jì)隨峰的唇。《女仆被调教成荡妇》喬唯一無(wú)奈看她一眼,頓了頓才又道:他沒(méi)有一定要來(lái)的義務(wù),況且不來(lái)也挺好。
鐵玄見(jiàn)聶遠(yuǎn)喬這神色變幻莫測(cè),一時(shí)間也揣摩不明白聶遠(yuǎn)喬想著什么了。《女仆被调教成荡妇》張秀娥抿了抿唇,自己應(yīng)該如何面對(duì)聶遠(yuǎn)喬?
陶氏是一萬(wàn)個(gè)不想去,這地方這么晦氣,誰(shuí)愿意進(jìn)去啊?《女仆被调教成荡妇》張秀娥的心中暗道不好,因?yàn)楹捅娙艘黄饋?lái)回來(lái)的,她也沒(méi)好意思在村子外面的地方下車(chē)。
張雪巖打開(kāi)屋里的燈,光從門(mén)口流瀉出來(lái),宋垣躺在地上,后背倚著墻,歪歪扭扭地瞇著眼睛看著張雪巖。《女仆被调教成荡妇》從初中開(kāi)始,每年的忌日蔣慕沉都會(huì)回來(lái)這邊,一待便是大半個(gè)月,開(kāi)始還挺常回他這邊的,到后來(lái)連這邊的家也不回來(lái)了,高中之后,就自己去外面租了房子,一個(gè)人住著。
著作權(quán)歸原作者所有,任何形式的轉(zhuǎn)載都請(qǐng)聯(lián)系原作者獲得授權(quán)并注明出處。